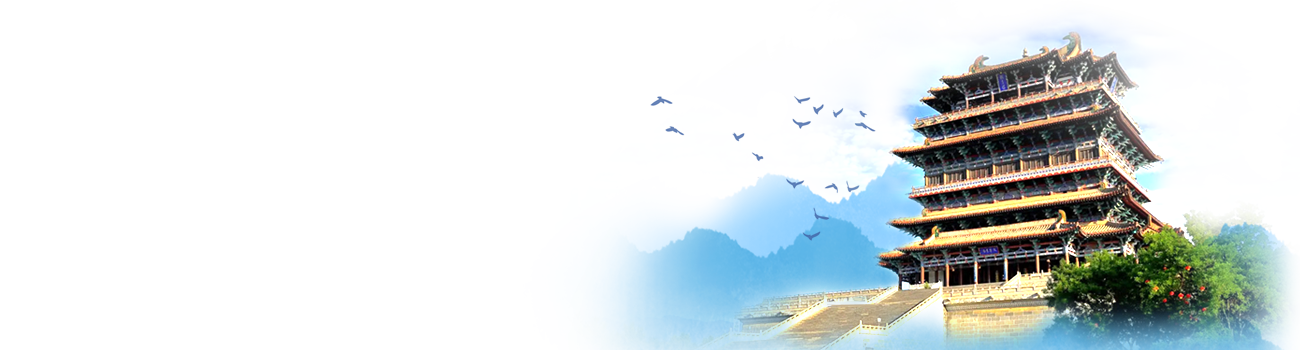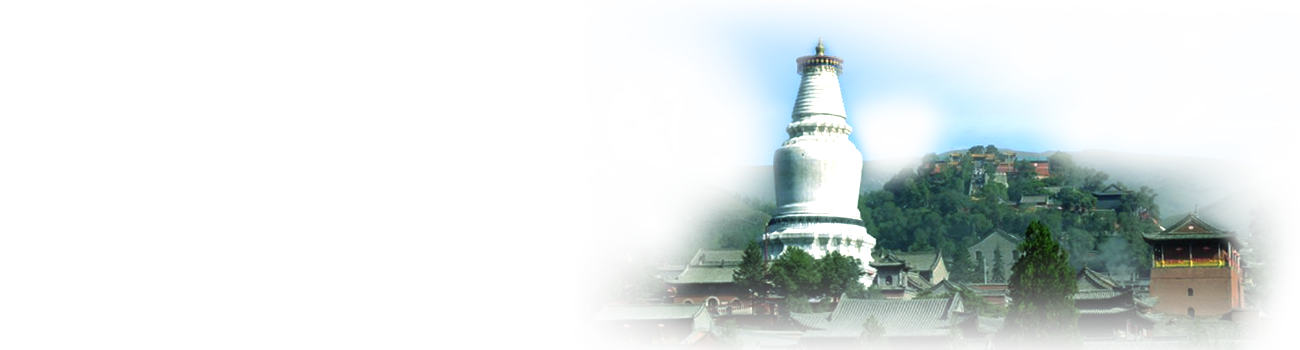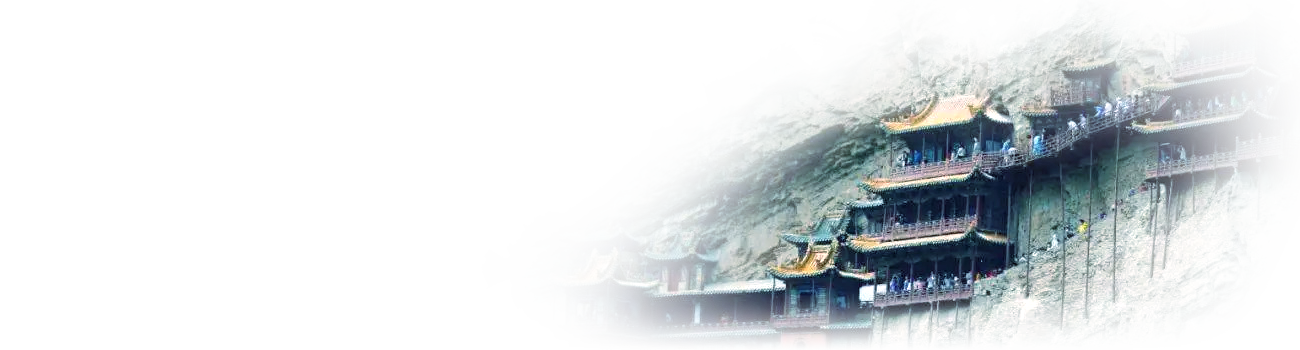考古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帝尧天文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帝尧是一个关键人物。《尚书•尧典》中有一大段记载帝尧从事与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有关的活动: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一段关于天文学的记载标志着中华文明独有的天文学体系已经诞生。天文历法由官方掌握,以崇敬的态度观测天象并制定历法,一年分为四季,历法采用阴阳合历,将赤道附近恒星的黄昏南中与季节对应起来。时间上的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与空间上的东、南、西、北四方相对应,这是后来五行化的宇宙观的滥觞。
考古发现印证了《尧典》的记载。陶寺观象台证明帝尧时代不仅进行了天文观测,而且还建造了大型的观象设施;陶寺圭表的确认表明帝尧时代同时进行了多种天文观测。但是,由此也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陶寺考古发现的天文遗迹似乎与《尧典》记载的天文活动并不一致。陶寺考古展示出来的利用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的方法和利用圭表观测正午日影的方法在《尧典》中并无记载,而《尧典》中记载的四仲中星观测在陶寺遗址中又未见痕迹。那么,《尧典》中记载的天文历法与陶寺发现的天文遗迹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要从《尧典》的记载和陶寺天文遗迹二者的天文学内涵来分析。
通常认为《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观测是为了确定二分二至日,但是实际上,观测四仲中星不能确定准确的二分二至日,也无法得到比较准确的回归年长度。第一,如果严格依靠观测昏中星来确定季节,要对“昏”有明确的定义,如现在天文学以日入地平6°为民用昏影终的标准。然而事实上黄昏时刚开始能看见星的时刻很难界定,并且亮度不同的恒星能够观测到的情况也不同,在计时仪器出现之前,古人在实际应用中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具有明确天文学意义的“昏”的标准来观测中天的星进而确定准确的节气日。第二,因为恒星在天上不是连续的,所以无法保证在特定节气日期、标准的昏的时刻、正南方子午线上有一颗明亮的恒星,这一点中国后世历法看得很清楚,汉代以来历法中给出的严格意义上的昏旦中星并非具体的恒星,而是计算得到的某宿多少度,类似于现代天文学的赤经的度数。第三,中星虽然可以和寒暑相联系,但是二分二至的概念不可能通过观测昏中星确定,只有通过观测太阳的南北变化才能确定二分二至,经过多年的观测得到回归年的长度。
所以,帝尧时代的天文学不会是通过观测中星来确定二分二至日,而只能是通过观测太阳得到二分二至日,结合对月亮的观测,建立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然后按照历法推步得到二分二至日观测四仲中星。当时如何观测太阳和月亮,《尧典》中没有具体记载,陶寺观象台和圭表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陶寺观象台由向东的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组成,共有12条观测缝,既有明确的冬至、夏至观测缝,也有非常接近春秋分的观测缝,因此整个观象台无疑是为了观测日出方位的变化而精心设计的。用这样的设施长期观测,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回归年长度,并形成推步历法。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另一种重要的天文仪器,就是圭表。其中作为立表的杆子,其长度与陶寺时期的尺寸和古文献中记载的八尺表长正相吻合,而作为圭尺使用的漆杆,在与夏至影长相应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标记,应该是用来测量夏至影长的。圭表测影是中国古代确定回归年长度的传统方法。
因此,《尧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是通过陶寺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量正午日影两种方法共同得到的。
《尧典》中的“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表明当时历法是阴阳合历,以朔望月为月。陶寺观象台最南端的1号缝不能用于观测日出,但恰好可以用来观测月亮升起的最南点,这表明当时对月亮已经进行了长期细致的观察,因此把朔望月作为历法中的一个时间单位是符合当时天文学发展状况的。
观测中星不是为了确定二分二至,而是一种“月令”式的对自然的观察。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会认识到,到了某一季节,天空会出现什么样的星象,植物和动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夏小正》、《礼记•月令》等文献中都是如此记载。中星的观测不需要特殊的仪器,在考古中很难找到遗迹。
《尧典》中与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有关的官员共有6种: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他们的分职有所不同。其中羲与和负责总的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则被分别派到四方观测四仲中星,举行相关的迎日、送日仪式,并观察相应季节的民事活动和鸟兽等物候变化。从这样的分工看,羲、和二官职执掌的任务较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执掌的更加重要。但是《尧典》这一段总共164个字中,记载羲、和的只有42个字,而记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却占了122个字。这样记载的原因在于,《尧典》是一部政论性著作而非专门的天文学著作。后世天文官的天文仪器制造、使用仪器观测、历法推步的“术文”等具体天文工作都是在《天文志》、《历法志》一类的专门篇章中记载,从这点看《尧典》对羲、和的工作未予详细记载实属正常。而“分派官员到四方观测中星和民事”这件事情本身以及各地顺应天时的民事活动属于国家行政和民生一类的事务,因此《尧典》记载更加详细。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揭示的正是《尧典》未加详细记载的羲、和二官职的天文工作。
由此可见,《尧典》详细记载的四仲中星观测只是当时天文学的一个侧面,当时天文学的主要方面《尧典》并未详记,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正是《尧典》不曾详细记载的当时天文学的主要方面。因此可以说,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互补,揭示了帝尧时代中国天文学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