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圉城夜月”明 文姬耀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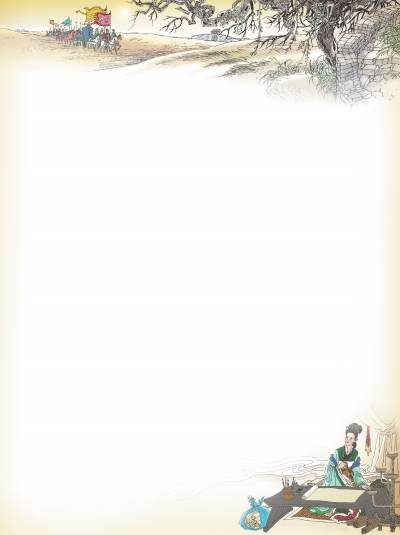
图/王伟宾

□冬夏
公元208年。某日,大漠上驰来一支胡汉混杂的马队。忽然间,狂风卷起漫天沙尘,大家惊呼:“保护好夫人!”
34岁的蔡文姬端坐马上,脸上已有了岁月的风尘。12年胡地生活,她早已不惧雨雪风霜,但谁知她内心无边的苍凉?
去留两难。故乡中原在这头,两个孩子在那头,一边牵着游子刻骨乡愁,一边牵着无边深邃的母爱。
尘埃落定,马队欢呼,但文姬内心凄然,她内心的沙尘暴仍无止息,《胡笳十八拍》旋律正缓缓响起。
蔡琰,又名文姬,河南杞县圉镇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集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于一体的女性”。
《后汉书·烈女传》评价蔡文姬:“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她通音律,十岁辨弦断之音。她精书法,学父亲蔡邕隶书,得其神韵,丰筋多力。她留下的文学作品光照千古,《悲愤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被誉为建安叙事诗“双璧”。她的《胡笳十八拍》,被郭沫若赞为“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
她一生颠沛流离,婚嫁三次,命运丰富奇特,饱尝生离死别。
历代文姬画像多种,面容多带刚毅之色,她的美丽,是坚硬的。
她的人生波澜壮阔,因此拥有“中国女诗人中最辽阔的视野”。
家学造就了她,常人无力担当的悲情命运造就了她。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圉城夜月”,曾是她的故乡杞县圉镇十景之一,夜月清明,光照千秋蔡家女,魂兮归来!
◎故园井曾映惊鸿影
《汉书》称,蔡文姬为东汉陈留郡圉人。陈留郡圉县,自商汤封夏后于杞地时开始建城,西汉时颇具规模,设圉县,治所设此,是历史名镇。
夏日,寻访蔡氏遗迹,抵圉镇时,正遇大雨。
蔡文姬之父蔡邕,字伯喈,生于公元132年,卒于公元192年。蔡家祖籍关陇一带,文姬高祖辈迁圉县。
圉镇镇北头十字路口,塑有汉白玉蔡文姬立像,娟而不媚,清而不寒,手握竹简,侧身微俯,周围有多块诗碑,分刻《胡笳十八拍》等,碑上字迹有脱落。
文姬像周围,是小镇最热闹所在,环境略显脏乱。
镇东头公路边,有“蔡邕蔡文姬纪念馆”,为安徽出版集团资深出版人李旭个人所办。
纪念馆是两层小楼,楼上,设多个陈列柜,整齐放置李旭多年收集的资料、图册、画像等。
纪念馆由李旭之父李存忠管理。李存忠是圉镇本地人,今年76岁,开封师范毕业后,一直在镇上教学,直至退休。
“纪念馆建在俺家宅基地上,花了不少钱。建成后公益性开放,不收费。为啥要办纪念馆?蔡邕、蔡文姬父女,是俺家乡的骄傲,作为后人,要好好纪念他们。”李存忠讲得很朴素。
镇上有小街名叫蔡白街,长800米。李存忠说,街名原本叫蔡伯喈,时间久了,传成这几个字眼。
在李存忠带领下,我们寻找蔡家花园——相传蔡家故居所在地。
从蔡白街转入一条小胡同——文姬胡同,走上十几步,见一片废弃荒地,生满野草杂树。荒地旁,立黑色石碑,上书“蔡邕故里”。
该碑西侧数步,另有一块黑色石碑,上书“文姬井”。碑后有井,井口被石板盖得严严的。
镇上老人告知,蔡家是当地望族,宅院壮丽,后来都毁弃了,惟余这片废弃荒地。相传蔡家花园内原有井七眼,六眼被泥沙淤平,只剩这眼文姬井,水质好,没有碱,好喝。淘井时,还从里头淘出一些粗陶罐。
设想1800余年前,文姬在自家花园中嬉戏,井水清清,曾映照过她清朗如月的面容。
公元174年(一说是177年)6月,蔡文姬出生于蔡家故宅里,母亲赵五娘知书达理,与蔡邕琴瑟和谐,蔡邕45岁时赵五娘才生了文姬,作为独生女,她很受宠。
公元178年,文姬随父母一起被流放到现在的包头阴山南部一带。后来她又随父亲流落到江南会稽。
10余岁,文姬回归故里,直到16岁嫁给卫仲道。18岁时,丈夫过世,文姬再回娘家圉镇。20余岁时“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12年”。后被曹操用重金赎回,嫁给了董祀。
20余岁以后的蔡文姬,离故乡渐行渐远。她卒年不详,逝后葬于陕西蓝田县。现蓝田仍存文姬墓,建有纪念馆。
河南尉氏县蔡庄,有地方学者称蔡庄是“文姬故里”。杞县尉氏两地,争和文姬认乡亲,也是中原人表达热爱的方式吧!
在圉镇,蔡家父女之名,紧密相连。文姬成就,来自父亲培养。
《三字经》上说,“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宋代朱文长《琴史》记载,文姬10岁时,中秋夜祭月,蔡邕室外弹琴,室内文姬听到父亲弦断之音,马上说,第二根弦断了。蔡邕又故意弄断第四根弦,文姬马上明辨。蔡邕开始教女儿学琴,两年后,文姬琴艺学成。
文姬过目不忘,诵读诗文,竟能一字不落地背出父亲藏书中400多篇文章。
蔡邕是书法大家,隶书稳重端庄又飘逸顿挫,人称“八分体”。
河南博物院馆藏蔡邕书写“熹平石经”残片,“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范文澜称赞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最高境界。”
所谓“熹平石经”,是汉灵帝时,蔡邕校书东观,经籍多有谬误,为之订正并书写镌刻在石碑上,立在大学门外,学子都就此石经校正经书,每日观览摩写者不绝于途,此即为“熹平石经”。
文姬全面继承了父亲多种才能,在文学殿堂上,父女俩的光芒交相辉映。
◎明月之下念文姬
圉镇,流传多个和蔡文姬相关的美丽传说。
有老人告知,文姬是赵五娘梦见有托钵僧送她一颗兰花籽,因此孕育了文姬。
相传文姬满百天正逢重阳,一派节日喜气中,文姬“抓周”,小手一下抓住了毛笔。
历代相传的“杞县八景”中第二景名“圉城夜月”,和文姬大有干系。当地人传说,文姬精通音律,蔡邕把焦尾琴传给了她。留居匈奴12年中,她思念故乡亲人,常坐对明月弹琴,有时伏在琴边睡去,梦魂随月亮回到故乡。日子久了,她的影子印到了月亮之上。
圉镇原有望月楼,乡亲上望月楼赏月时,会发现月亮上的文姬身影。每到夏秋季节,圉镇人争相上望月楼赏月,缅怀蔡文姬。
《杞地笔记》还记载,从清至今,每到中秋节晚上,皓月当空,圉镇笼罩在朦胧月纱之中,乡亲们成群结队走到北门里望月楼旧址,席地而坐,边赏月边怀念蔡氏父女,诉说对远方亲人思念之情。
有诗人咏叹此景:“晚到圉城望,长空幻影多,金波涵古碟,皓皓走黄河,天延浮云散,秋方候燕过,何人烟霭里,子夜弄新歌。”
文姬流落匈奴时,不但家乡父老念着她,还有一个人,始终关注着她。他就是曹操。
曹操有雄才大略,“姿貌短小,神明英发”。
曹操又霸气,总将事情做得决绝,让天下为之一愣,继而永留史册。“文姬归汉”,便是如此。曹操赎回文姬,下了大本钱——“白璧一双,黄金千两”。
郭沫若评价道:“他(曹操)之所以赎回蔡文姬,是从文化观点出发,并非纯粹出于私人感情。他之所以能赎回蔡文姬,并不单纯靠金璧收买,有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的。”
归不归汉,文姬有选择可能吗?
她没有。匈奴不敢留她。她对故国思念、对父亲未竟事业的自觉责任,都会让她选择回家。
匈奴有“收继婚”制度,汉族女子很难接受,也会让她选择离开。但孩子是南匈奴王子,不可能带走。生离,就是死别。
她在《悲愤诗》里写了这样的场景,“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如斯场景,会让一个母亲发疯。
回家关山无数,离孩子越来越远。绝望的怜子之情,让她感到自己被上苍抛弃,她如怒涛般的感情爆发,她一路弹唱,遂有《胡笳十八拍》。
男人的理智是逻辑,与感情异质,易在感情冲击下溃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觉,与感情同质,能在感情汹涌中保持完好。文姬以理智与情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惊心动魄的境界”,这就是《胡笳十八拍》。这是文姬写给自己与孩子的。
归汉后,她的日月如何?
第三任丈夫董祀奉曹操之命才娶的她,他是正当好年华的美男子。蔡文姬已育有两子,经胡地12年风霜,再经与孩子生离,面目内心,再难“岁月静好”。
“归汉”后的文姬,任何一个男子、任何一种爱情,都难以弥合她内心的残缺了。
文姬归汉,把自我灵魂永远放逐,永难拾回。无论是《胡笳十八拍》还是《悲愤诗》,这是文学中的丰碑,却埋葬了一个女子整整一生。
◎“东汉人中力量最大”
蔡文姬的《悲愤诗》,历来评价极高。它以500余字的长篇叙事,记录在汉末动乱中,人民的痛苦与诗人自身的悲惨遭遇。
其诗作,既表现了建安文学“五言腾踊”的风格,又充分体现建安文学“慷慨多气”“俊才云蒸”的气象。
描绘战乱,曹操曾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文姬在《悲愤诗》中道:“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景象更凄惨。
清代大学者沈德潜《古诗源》中称:“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生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这是惊世骇俗之论了。
蔡文姬写《胡笳十八拍》,起首句,便展示了“中国女诗人中最辽阔的视野”:
“我生之初尚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它宏大到从何进讲到十常侍再讲到董卓,把一己命运放到历史大旋涡中去。女人中绝无仅有。
《胡笳十八拍》中,举目皆是“心愤怨、自悲嗟、我最苦、空断肠、气将咽、泪成血、彻心髓、号失声、肝肠绞刺、叹息欲绝……”饱受命运凌虐,血泪是她“天问”的武器。
她之前的秦末,有孟姜女,用血泪为武器,哭倒长城。这是民间传说描述的一场伟大的“性别与政治”战争,是一次稀少的女性胜利。
从孟姜女到蔡文姬,女性神威依然在,女性的绝望愤怒惊天动地。一部《胡笳十八拍》,始于“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终于“苦我怨气兮浩于太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
“其气象不羁而难浑,其痛苦绞肠滴血,其悲愤如滚滚怒涛,将天地神抵都诅咒了,绝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的。”郭沫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