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洎河畔春烂漫 花都一入迷望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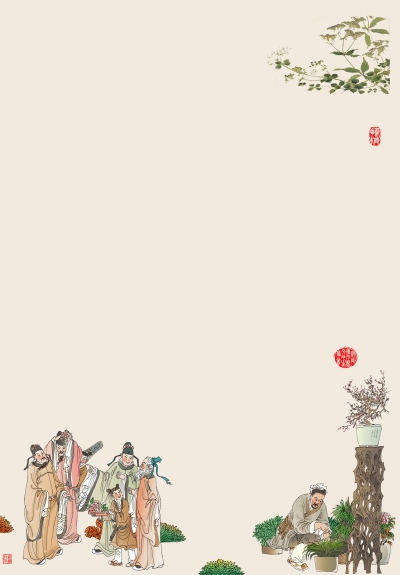
蕳选自《诗经名物图解》,由日本细井徇/细井东阳绘制出版于1848年
图/王伟宾
□河南日报记者 赵慎珠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乘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诗经·郑风》中的《溱洧》,描述了2000多年前初春的欢乐景象:溱水洧水,绿波荡漾,男男女女,手拿兰草游乐,有少男少女相互戏谑,送一支芍药私订约期。
民歌流行的春秋时期溱洧一带,就是今天鄢陵的双洎河畔。
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在两枝花的俏丽出场:兰草与芍药。凭借两种芬芳的花草,一首诗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青春的转换。
一枝一叶,灵性生动,漂流在文学的长河中,跃动至今。一草一木,姹紫嫣红,年年开遍鄢陵,令人心动。
◎“一入鄢陵望眼迷”
春山苍苍,春水洋洋,玉兰、海棠、杏花、桃花次第开放,随后的四月、五月,或是更多的月份,百花纷至沓来,花花世界,灿若云锦。
每一片泥土铺就的地域,每一处乡村或城镇,每一条大街小巷,只要在这里的土地上,就有色彩和花朵,杂花生树,花海涨潮,以致明代江西巡抚曹汴留下一句:“一入鄢陵望眼迷”。
鄢陵与花木结缘,由来已久。
盛唐时代,这里出现了大型园林植物的栽培,《鄢陵县志》记载,在县城西大街路北,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存有园中湖遗迹。
北宋,这里花木栽培业兴盛,有了以养花为生的农户,培育出京城所需的盆花、插花和菊花、蜡梅等花卉,鄢陵境内建起官家私有的大型综合园林。
北宋末期和南宋初年,兵祸战乱,鄢陵人多避难于江南一带,花木栽培技艺也随之南下,广为传播。
明代,鄢陵人大户辟大园,小户建中园,构成了以县城为中心,方圆数十里,规模宏大的花卉栽培区域,形成50余处规模不等的私家园林,陈参议家花园“桃花延袤十里”,刘尚书家花园花卉繁多,“千里之外一时称名园”……专供出卖花卉苗木的花圃应时而生,花卉销售也延伸到南京、西安、汉口、寿州等地,时人称鄢陵为“花都”。
清代,这里花木中的盆景造型独树一帜,以桧柏盘扎成鸟、兽或建筑物形状,或制作盆景桩景,自成体系。清《鄢署纪闻》载:鄢陵称花县,西乡姚庄编户皆艺花。
花香蝶自来。稍稍翻阅一下鄢陵文学史,会发现孟浩然、李白、范仲淹、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等名家的身影,他们都曾驻足鄢陵,吟诗作画,咏花叹景。
◎“但见红云冉冉来”
鄢陵花木甲天下,缘于人们赏花、护花,缘于中国人心中一份浓郁、清澈的爱花之情,一种精致生活的雅趣。
我国有纪念百花生日的“花朝节”,最早记载于春秋时期的《陶朱公书》。唐武则天时期,从官府到民间,流行花朝节的习俗。宋花朝节的日期定为二月初二或二月十二。《广群芳谱·天时谱二》引用《翰墨记》:“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又引用南宋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东京(今开封)二月十二曰花朝”。
唐人爱花,爱得热烈而富激情。
李白眼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孟浩然笔下“荷花送香气,竹露滴清响”,都来得直抒胸臆。
唐代的花魁为牡丹,新折的牡丹是唐人的最爱,能工巧匠雕琢而出的牡丹,同样备受推崇,在唐代的金银织锦、漆器金银器、石刻彩绘中,随处可见生机盎然的牡丹形态。
唐代的花卉装饰,富丽华美,在金银器、瓷器、丝毛织染,或是石雕、壁画、佛窟中,缠枝花纹“翻转仰合,动静背向”,收放自如,尽情展示盛唐气象。
宋人爱花,爱得优雅而有才情。
一到花期,洛阳城内,王公贵族或是贩夫走卒,无论贵贱,满城赏花,人尽插花。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也写道:宋代遇喜庆大典、佳节良辰、帝王出行,公卿百官骑从卫士无不簪花,帝王本人亦不例外。
《东京梦华录》记载,皇帝一高兴,就会赐花,大臣以接受皇帝簪花为荣,所簪之花则以名花为贵。
想象一下《武林旧事》中的画面,就很热烈:“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真是无花不欢。
女子簪花照镜,为悦己者容;男子簪花回望,风雅时尚。苏轼笑自己:“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黄庭坚调侃:“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一声“羞羞”,几许洒脱。
百姓爱花且不俗。宋代的清明节,杭州人折来西湖绿柳,遍插门楣,街衢巷坊之间,便是望不尽的碧云翠雾,散不完的幽幽清香。到了五月端午,杭州遍城插花,家家门前的青瓷、白瓷花瓶中,插上桃枝、柳枝、石榴、蜀葵、浦叶、栀子花……
文人墨客爱花,入诗入画。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书中提到,“岁朝清供”是中国画家爱画的画题,明清以后画的更多。画中多是天竹果、蜡梅花、水仙,皆取其颜色艳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空对,眼目増明,是岁朝乐事。
◎“鄢陵据形胜天地生豪酋”
“鄢陵据形胜,天地生豪酋”,唐代诗人孟浩然对这里赞赏有加。
鄢陵位于许昌市区东部,属黄河冲积平原,地下水资源丰富,土体深厚,耕层疏松,70%的土地适宜种植花卉。这里泉甘土肥,气候宜人,非常适宜南北不同气候、土壤条件下各种植物的生长。
1986年版《鄢陵县志》的主编司晓辉说,花木在鄢陵经过1—2年的驯化,北移南植的成活率比直接移植高50%以上,枇杷、石楠、棕榈等南方观赏树木,比直接移植到黄河以北的成活率高10%—15%。这里是沟通南北花卉的桥梁。
鄢陵地处古代黄河农业带的中心,是中国野生植物向农业驯化、进化的重要地带。不同的是,当黄河流域的先民孜孜不倦地驯化农作物小麦和谷物时,鄢陵人却把目光停留在了植物的审美功能上,他们对观赏花卉进行驯化、培养,向世人贡献了鲜花和美丽。
北宋都城开封,养花之风大盛,对花木需求激增,凡是东京市场所需的,在鄢陵的园圃中都能找到。那时有河流从开封经鄢陵南流过,漕运通畅,水陆交通便利,专门从事花木贩运的行当应运而生。
明代读书之风盛行,5万人口的小县鄢陵,出了20多名进士,还有一榜五进士的奇迹。鄢陵籍官吏充满朝野,人称:“朱明天下鄢半朝”。这些官员的足迹遍及江苏、福建、浙江、湖北等地,把鄢陵花卉带向各地,又把所任地的奇花异草带回鄢陵,当地花匠成功培育了山茶、茉莉、日本菊、朝鲜牡丹等多种园林观赏植物。嘉靖《鄢陵志》载:花卉名种甚多。
时光流逝,花开依然。
1958年,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前身)的一批师生,在著名花专家、陈俊愉教授的带领下,来到鄢陵。他们拜花农为师,收集整理花木栽培方法和技术。
他们发现,当地花农多处体现了因地、因时、因物制宜的独创性:繁殖苗木时,花农注意切削部位与砧木叶芽着生的位置,不仅提高了嫁接成活率,还能促使苗木生长旺盛;施用“矾肥水”于酸性花木的一套完整经验,更是花农的一个创举,它使栀子、杜鹃和柑橘等在北方很难培养的花木枝繁叶茂,取得国内外园林界前所未有的宝贵经验。
◎“鄢陵蜡梅冠天下”
一株蜡梅,几点梅花,山雀一双,相依相偎。用生漆点化禽鸟秀眼,是宋代徽宗皇帝赵佶最为独特的技法。
小诗一首,是徽宗独创的瘦金体,更让一副杰作《蜡梅山禽图》古韵弥散。
这幅画作,现深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整幅画作中最引人入胜的,是黄色的蜡梅花,似有清香袭来。
徽宗爱梅,在《梅竹聚禽图》和《腊梅双禽图》等画作中,都能感受得到,蜡梅在北宋宫廷内的尊贵地位,约略可见。
蜡梅来自鄢陵,它醉倒过徽宗皇帝,也倾倒了寻常看客。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蜡梅,释名黄花梅,此物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清初《花镜》载:蜡梅俗称腊梅,一名黄梅,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放,其香又近似,色似蜜蜡,腊月开放,故有是名。
清代刑部尚书王士禛,用“梅开腊月一杯酒,鄢陵蜡梅冠天下”的诗句,让鄢陵蜡梅名扬四海。
岁月悠悠,梅香不绝。
1988年1月,24株蜡梅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飞越浩瀚的太平洋,扎根于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迎朔风绽放,沁香扑鼻。
1999年1月,9株蜡梅移植在中南海紫光阁,亭亭玉立,偌大名园流溢着蜡梅芬芳。
若冬日到鄢陵,便是街街有蜡梅,家家飘花香,冬寒料峭中踏雪寻梅,诗意盎然。
3月7日,在鄢陵县新科园林的百亩园林内,黄色蜡梅花尚存,红梅花娇艳怒放,清香阵阵。
56岁的“老花匠”于发科,从1987年开始,潜心培育蜡梅。他从神农架引进野生蜡梅的古桩,进行嫁接,几番捏、扎、绑、拉、剪的工序,育桩、嫁接、修剪、上盆的步骤,历经几年甚至十几年,培育成古桩蜡梅盆景造型,多次在全国“梅花蜡梅展”上获奖……
绚丽的阳光,照亮了明净无尘的春景,“青春都一饷”,且去看那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