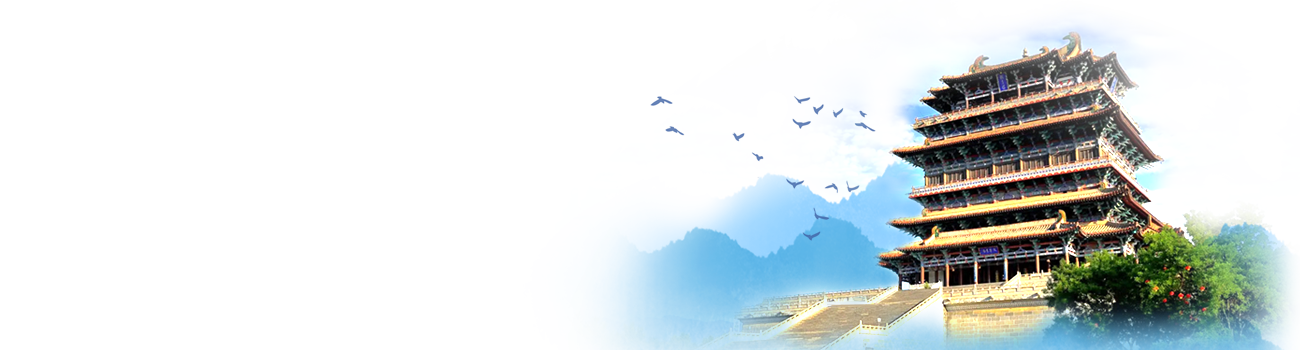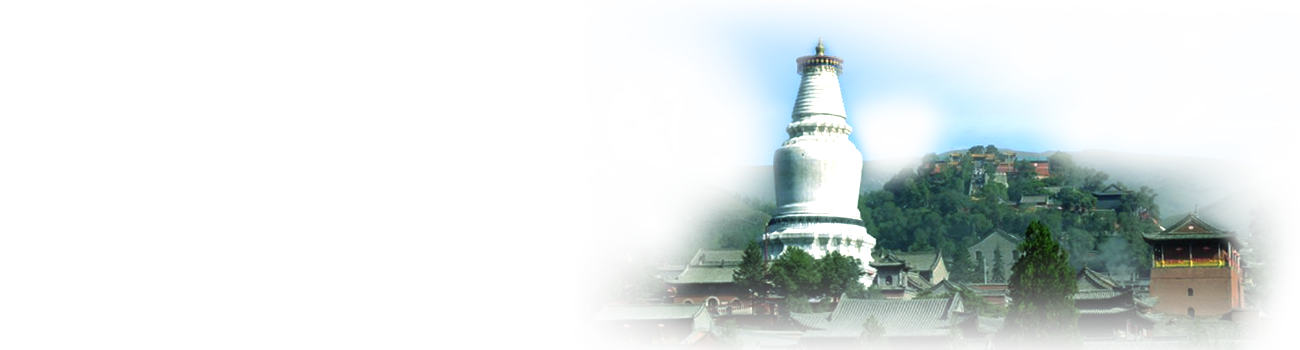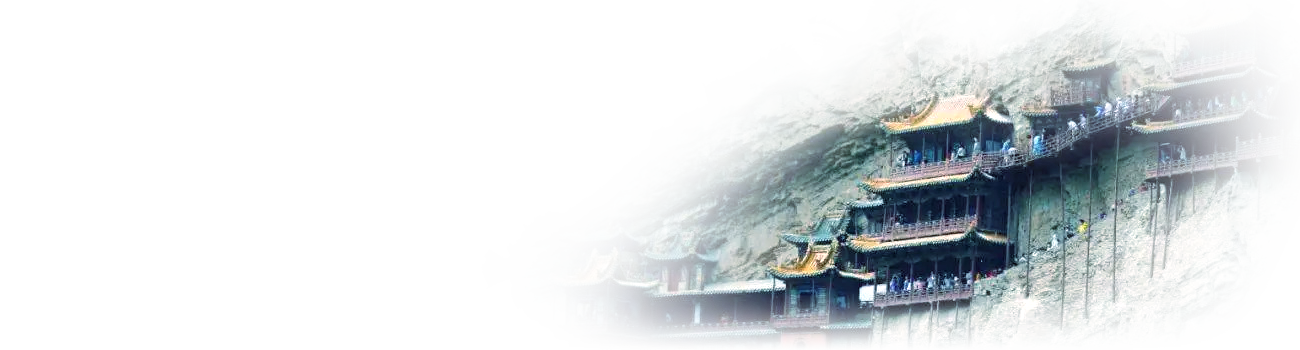司马光:千年毁誉下的千秋功业
发布时间:2021-09-08 08:10:02
寻访地理:夏县小晁村
寻访人物:司马光
车在大运路上往运城方向走,临近夏县县城前十公里左右有一个向西的路口,通向水头镇,路边有几个学龄儿童在追打嬉戏,将小石子抛起,击打路边来往的车辆。我的思绪飘飞,九百多年前,那个孩子将大石砸向水缸的沉稳与机智的背后,是否有与他们一样的顽劣。
时隔太久,我们已无法揣测这件年少英雄的事件对司马光以后的仕途有多少帮助,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之所以砸缸救人可以在世人口中代代相传,不是因其年少的智慧,而是因其后半生地位和声名。
当年,在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场面极为壮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官吏,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哀悼,实属罕见。
从水头路口到司马家族的坟茔,要走将近半小时的路程。我的视线随着车辆的起伏而颠簸,透过车窗,能看见大片的原野和一闪而过的树木。身边是安静的,恬淡的,包括蓝天白云。
一直到我下车看到司马温公的祠堂在眼前逶迤展开,我都没有从这种感觉里走出来,没有敬畏与惊叹,没有悬疑与窥视,我只是安静地走近它,走近它绿柳成荫的温和。
墓葬在小晁村北侧一华里,东西长302米,南北宽190米,占地面积近百亩,茔地现存司马光及其父兄亲属墓冢封土堆13座,背依鸣条岗,前临故都安邑,方圆平旷疏阔,阡陌交错。
在松柏翠绿的萦绕中,这块墓地安静祥和,与他生前官场的诡秘和政潮的汹涌了无瓜葛。
透过长长的甬道,是司马家族的家庙。这是一四合院,庙内供有司马光以及他的父亲兄弟的塑像,院中翠竹依依,清静整洁,曾由族中人共同维护与供奉。
其实,这份清净差点遭遇灭顶之灾。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出现在政坛最高层的章惇宰相,以王安石事业继承人的姿态,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敌,他甚至提出,要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好在同僚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免得冤冤相报,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念头,保留了此处的清静。
司马光的两部书
相传,在很多人拜访司马光的时候,总要问人家一些使人很难堪的问题,家里有没有钱?开支够不够?诸如此类。被问的人都很奇怪,觉得怎么会问到这种怪问题。原来司马光的标准是,一个人有钱,能维持生活,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才会有独立的人格。
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
典地葬妻并不如司马光年少时砸缸更为出名,但更能彰显个人修养。
对于个人修养,司马光看得很重。他曾经说: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智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有两部书:一部是《资治通鉴》,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必读;另一部就是《家范》。司马光自己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他说: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就研究立身处世和处理复杂的身边矛盾而言,《家范》确实比《资治通鉴》更重要更实用。
呕心作史15年 编出《资治通鉴》
我惊叹,在岁月浩瀚的烟波里,在多少场浩劫与小人的窥探中,墓地千年长存,规模颇巨。我更惊叹于那个枯瘦的老者,在酷暑寒冬,挥毫泼墨,15年如一日地在史卷中徘徊摘选,以毕生的精力为后人留下一部历史长卷。
千年前的一灯如豆,彻夜不熄,他的形容枯槁与几代兴亡一起在历史中定格。
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毕的稿卷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据说,《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他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博学到几乎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都非常熟稔,尤其是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在读史的过程中,他逐渐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以方便阅读的著史想法。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资君主治国之鉴。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而在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出走之后,著史更是他忠君报国的一条最直接的途径。
而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
司马光与王安石 执拗两相公
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派之后,曾经以他特有的方式,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遂成为政治死敌,不共戴天。
但两个人是互相钦佩的,钦佩对方的骨气。
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
公元1086年,司马光开始主持朝廷工作,以一年半时间将17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祐更化”。同样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著。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著。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从两位历史人物身上,人们不由得发出感喟: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
随着两位政治领袖的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过去的君子之争渐行渐远,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此就罕见这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政治家了。
反对的理性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从这里来说他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司马光在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与王安石比较起来,显然是有差距的。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如果说到数千年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和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却是望尘莫及。
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司马光这位史学宗师之赐。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人,在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冒着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来反对变法,我们无论怎么猜想,都可以断定,他们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上一定有着一个自以为“最崇高”的理由。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怎么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的名望。
我们可以猜想,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一直在担心:官吏们是否会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些担忧成为事实。
我们还可以猜想,当时,由于变法引发的社会动荡和来自民间的呻吟,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文人们激动了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力量。
所以,古墓仍在,浩气长存。 ■
本文作者:,摘自《山西晚报》
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