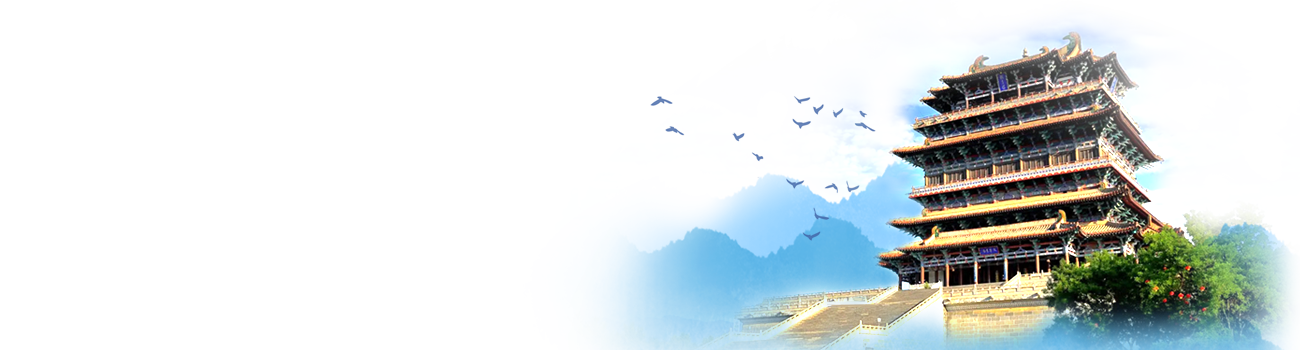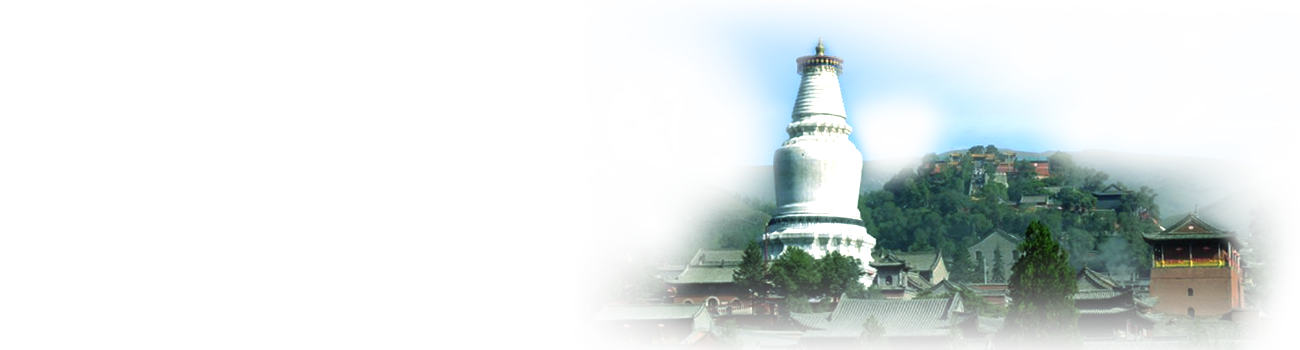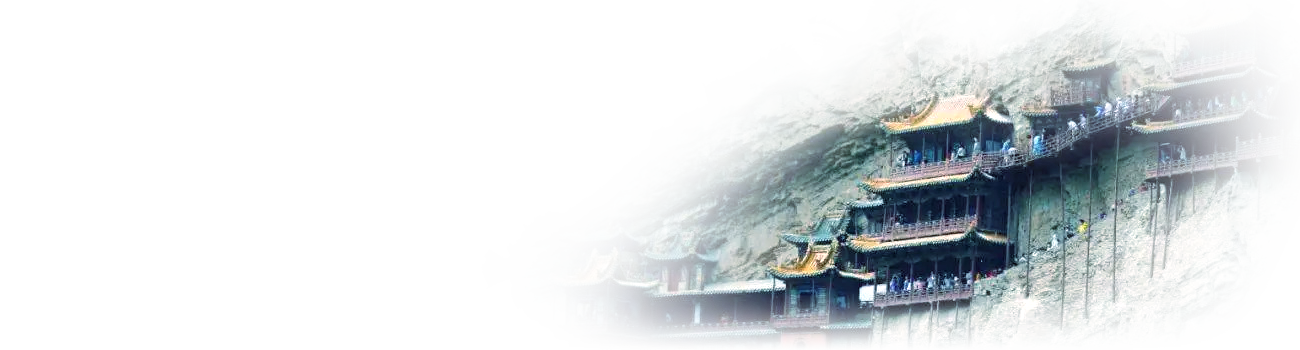元好问两朝文人的才情与担当
发布时间:2021-09-08 08:10:05
寻访人物:元好问
地理:忻州市韩岩村
你听过雁丘的故事吗?
1205年,金国一位16岁的少年赴并州赶考,途中碰到一个捕雁的人说,他今天捕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不止,然后投地而死。少年听后非常感动,从猎人手里买回了那只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边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并即兴感怀写出一首传世之作《摸鱼儿》:
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这少年名叫元好问,鲜卑拓跋氏后人,1190年生于山西秀容(今忻州市)韩岩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别号遗山,是名冠金元两代的诗坛巨擘。他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其间江山易主,风云动荡,遗山愤世吟诗、为官恤民、为士请愿、奔走存史,最终于1257年客死他乡。
诗词大家,遗珠累累;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2006年8月末的一天,细雨初停,阳光白花花地洒在油绿油绿的玉米叶上,我和忻州当地的两位朋友已经在一处紧锁的铁门外徘徊了半个小时。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寻访的元好问墓?那位生前为金元文化领军人物、身后引来历代名流大儒凭吊的元遗山之墓?
去年我曾寻访过毗邻的木芝村,传说中貂婵的故里,陵园荒草芜杂,一片衰色。当时就想,红颜香冢怎可与那气势豪迈的诗人史家之墓相比。不承想,这秀容之地在一个大家凋谢八百年之后竟也生出一样的怠慢。美人何其娇艳,巨匠何其风流,而如今都一样被遗忘在历史的尘烟中,何其悲凉。
铁门开来,里面的破败比外面的寂寞更甚,荒草没膝,断垣残碑,松榆蔽日。
这处陵园一为元墓,二为野史亭。元墓为元氏祖坟,坟内葬有元好问及其曾祖、祖父、生父、养父、长子、长孙。野史亭为元好问51岁时为修金史而建,“朱门万户凄凉尽,惟有元家野史亭”。此两处遗址历经数次修缮,内有金、元、明、清以来大量的名家诗文石刻,古迹斑驳,难以考究。好在记者在随后的寻访中找到了忻州市文管所孙转贤先生,关于这些碑刻,他曾做过详尽的搜集和注释。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八百年前的元遗山到底在历史上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和惆怅?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元好问曾在金朝出仕为官十余年,而在金亡后的20余年,元好问又像一个矢志不渝的文化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他长年奔波于晋冀鲁豫一带,宣扬儒学,搜集编撰金史。可是,他最想告诉后人的却是他对诗词的喜爱,他最为得意的大概也是他在诗词上的造诣,最沉重的是他以宣扬儒家文化、挽救天下斯文为己任。虽然他5次赴汴京应试,33岁才走入仕途,但“元才子”之名依旧誉满北国,“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他对自己的诗才也是极为自信。
元好问家学渊源,先祖元结为唐代著名诗人,父亲元德明诗才过人,不事雕饰。他被过继给叔父元格,元格对元好问的教育极为重视。元好问4岁读书,8岁学习作诗,后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6年。元好问认为“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而他的诗词修养也正是得益于此。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尤其是金亡前后的“丧乱诗”成为继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峰。“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造就了这些经典的旷世诗作。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写就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论诗三十首》,“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他提倡诗文刚健,反对纤弱,提倡天然,反对做作,提倡精练,反对繁冗。那年他才28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大众知之少矣。在大多数人心里,一代文坛领袖,就像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
野史亭上一布衣
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这时的元好问已是天命之年,他饱学诗书,不甘心从此放浪山水,他精于史学,曾任史官,久怀修史之愿。蒙古大军围困汴京之时,他曾请求携带国史出走,未被准许。此时,他再次萌生了编撰金史的念头,希望以自己“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的余力,做到国亡史存。为此,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
然而,元好问的修史志向并未得到新朝的支持,此后近二十年,元好问以一介布衣之身,每年都要为搜集史料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一部上百万字的史稿《壬辰杂编》,并汇编了北方两百多首诗作《中州集》。《中州集》以诗存史,不仅收诗作,而且带有人物评传。时隔六百年后,清代名臣五台徐继在拜谒野史亭时写下如下感慨:
“中都已弃汴京焚,累朝无复存文献。遗山乃构野史亭,河朔篇章搜罗遍。中州一集存巨编,微寓褒讥留小传。顿使金源生颜色,不与夏辽同鄙贱……”
夏、辽、金史料中,惟独金史较为完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史的许多内容来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
且莫独罪元遗山
1233年,对于两个王朝来说,是一个此亡彼立的新旧拐点,对于诗人元好问来说,同样是一个命运的转折,而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这里又隐藏着一段事关元好问名节的重大公案。
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这就历史上的“崔立碑事”。
元好问到底有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假使参与了,是不是有损其名节?后世诽议不断。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看来,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则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一个“独”字在这里是语气助词,不是单独的意思,郝经是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关于元好问气节问题的争议,崔立碑事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两个焦点:一个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如此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焦点就是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这似乎趋势逢迎。然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这在敬仰他的后人眼里似乎更像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 ■
本文作者:陈力方,摘自《山西晚报》
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