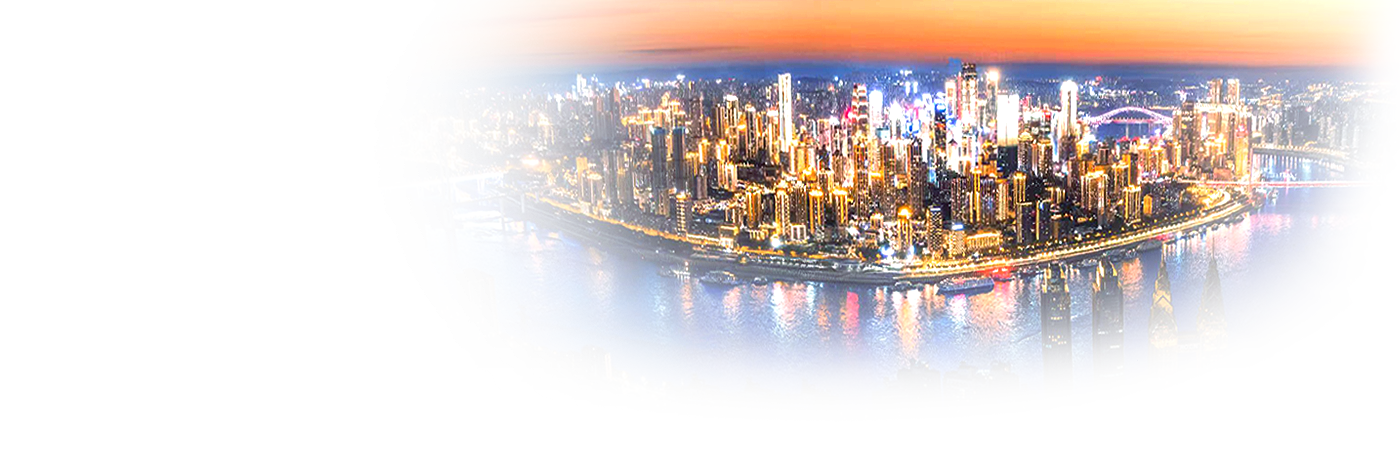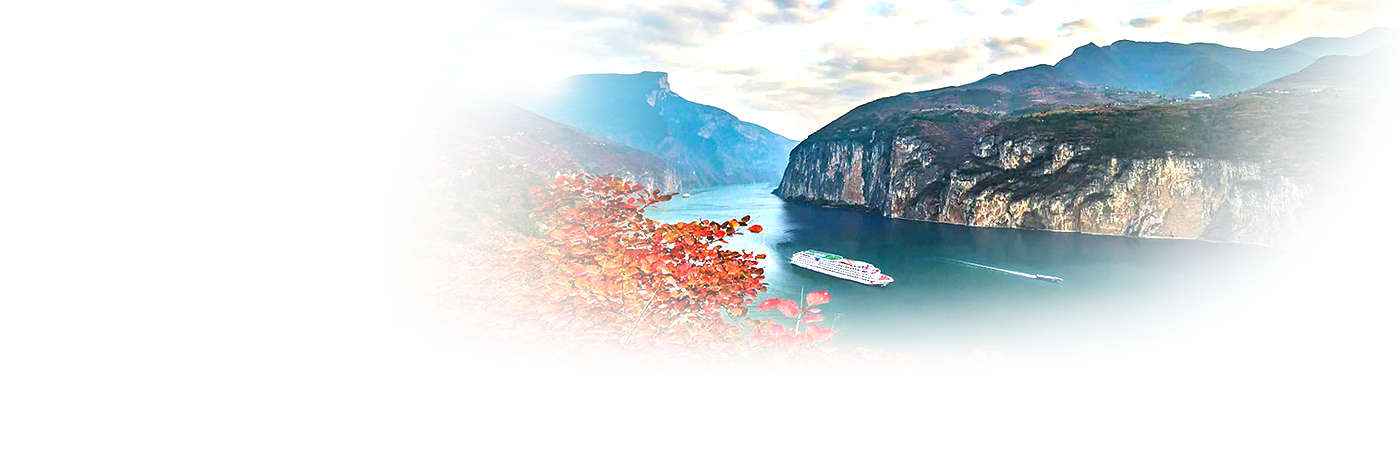侧记|翻译《格林童话》的那位爷爷,将“北极光”带回了母校
9月16日,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讲台上,87岁的杨武能教授以一曲口琴吹奏的《我爱你中国》打动全场。琴声悠扬而深情,仿佛每一个音符都浸润着他对家国与文学的炽热眷恋。曲声渐歇,余韵未绝之时,杨教授将刚刚获得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奖牌——这一国际翻译界的最高荣誉,郑重地交到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手中。
那一刻,不仅是一枚奖牌的传递,更是一种精神的交接,一段学术传统的延续。
这场由国际译联主办的语言盛会,自1999年问世,每三年一度,汇聚全球顶尖的语言使者。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颁奖典礼,被誉为“翻译界的诺贝尔奖”。那天,杨武能的名字被郑重念出,无数同行在线上线下共同见证。
“这份荣誉,属于所有为中国翻译事业默默耕耘的人。而我最初的信念,正是在川外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杨武能望着台下青年的面庞,声音温和却有力。
从山城十八梯出发 一生与德语相伴
1938年,杨武能出生在重庆十八梯下的厚慈街。山城的陡坡阶梯与火热气候,铸就了他坚韧而执着的性格。
少年时,他读到了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那颗年轻的心灵,被维特的激情与烦恼深深震撼。“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体验,”杨武能后来回忆道,“我仿佛透过译文,窥见了一个遥远而真实的精神世界。”
那本书,他反复捧读,纸页渐毛。命运的种子,在那一刻静默埋下。1956年,他考入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后因中苏关系变化,于1957年转学至南京大学攻读德语语言文学。在恩师叶逢植的指引下,他二年级便开始尝试翻译,195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译作,从此开启了漫长的文学翻译征程。
1962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外语学院任教。六七十年代的川外,条件朴素,但对于杨武能而言,这里同样是能够沉心学问的地方。他一边教学,一边继续钻研德语文学。无数个夜晚,歌乐山幽静深沉,而他书桌前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
“北极光” 映照六十载译路
87年人生历程,60余载翻译生涯,杨武能教授用毕生精力搭建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
《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格林童话全集》《海涅诗选》《魔山》……这些耳熟能详的德国文学经典,通过杨武能的译笔,走进了无数中国读者的心灵世界。尤其在八十年代,他所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掀起阅读热潮,成为一代人理解德国文学与情感启蒙的窗口。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艺术的再创造。”这是杨武能始终坚持的信条。在他看来,文学翻译家必须同时是学者和作家,他提出的“美玉与蜡泥”之说,强调文学翻译必须传递原文的文学美质。
2018年,他获得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而1983年,他已荣获享誉世界的德国洪堡奖学金,赴海德堡大学研修。作为国际公认的歌德研究权威,他是迄今唯一集歌德金质奖章、德国国家功勋奖章、洪堡学术奖金三大殊荣于一身的中国学者。
国际译联的颁奖词这样评价杨武能:“六十余年来,他活跃在德汉文学交流领域,以高质量译作将德国经典文学著作介绍到中国,帮助中国读者深入了解德国文学。”
这份荣誉背后,是逾百部译著的厚重积累,更是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长期对话。尽管获得国际最高认可,他至今仍会翻阅自己早期的译作,思考哪里可以进一步完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贯穿了他六十多年的翻译生涯。
秋日的阳光洒在校园里,一如多年前那个从南大毕业、初至川外的青年教师的身影。
仪式结束后,杨武能在师生的簇拥下走出大厅。奖牌留在了川外,这是一束光的回归。这束光,从重庆十八梯出发,照亮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书桌,温暖了歌乐山下的晨昏,辉映着德语文学经典的中文之路,最终闪耀在国际翻译界的最高舞台。
如今,这束“北极光”回到了他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将继续照亮后来者的路。正如杨武能所说:“我只是做了一个译者该做的事,而翻译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继续走下去。”
文/记者 秦思思 首席记者 林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