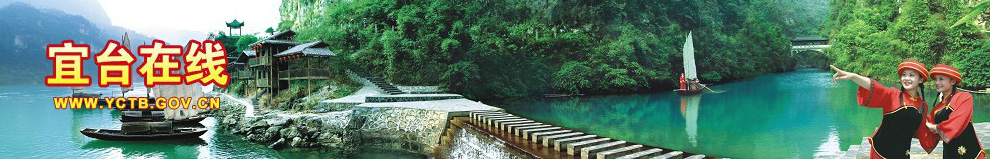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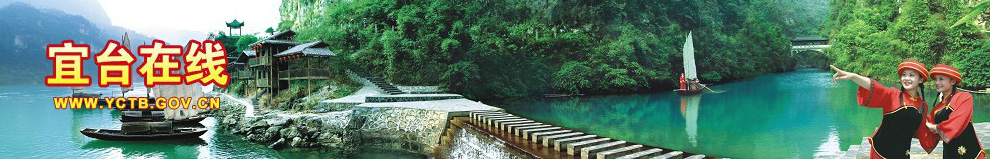
今年5月上旬,由湖北省省长王国生率团赴台举办的“台湾.湖北(武汉)周”一系列经贸洽谈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岛引起强烈反响。其间,专场湖北同乡会荡漾浓郁亲情。倘若在史册上各有褒贬的旅台军政要员彭善天上有灵,这位百岁世纪老人定会随之“叶落归根”。
古柏树见证人脉传承
黄陂横店彭郁湾有棵数百年的古柏树,已被编为武汉名树1016号。相传此树是从江西移民过来的彭氏,共有老祖宗所栽。到上世纪初,衍生于三大房和三小房的后裔按“文、人、正、启、光、荣、显、大”等论资排辈。
彭善属正字辈,1901年出生,字楚恒。1947年,升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区总司令,当年又因武汉大学“六一惨案”被撤职查办,1949年在汉乘“最后一趟飞机”赴台。因解放前后彭郁湾乡亲与其“荣辱与共”牵扯不开,故其家史和村史,颇不一般。
彭善父辈兄弟五人,他是四房老大,母亲早逝;其父先在河南烟厂当烟丝整理工,续娶河南继母再生一女一子:女双英嫁当地杨家务农,并为父送终;子鸿运后居香港。其父携家回汉后,在江岸永生里摆水果摊,爱打麻将,总叫“会算账”的大儿子在放学后边做作业边照看生意。
当年,横店王子寅田湾王老板在汉口做买办生意,路过时一眼相中勤奋聪慧的彭善当女儿王素琴的未来女婿,从此资助他相继上武昌圣约瑟教会中学、武昌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春季,他报考被录取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
王素琴与彭善共生六男三女,前后六子均早夭。大女儿启皖解放前后一直生活在武汉,退休前在武汉毛巾厂,积玉桥的老住房被拆后,这十几年都住在广州小儿家。二女启荧,三女启瑾,现都在重庆安度晚年。
日前,83岁的启皖阿姨在电话里回忆:“妈妈比爸爸还要大一岁!那时我们在重庆,确实对爸爸的事情一无所知;临解放前,妈妈坚决不要那张派人专送的赴台飞机票;解放后,政府安排妈妈带我们三个到汉源县做财会工作,屡被抄家、批斗,1969年妈妈病逝时还不到60岁......”
彭善与二房太太张毓芬共生五女三男,另住成都。建国初期,张太太才携子女转道香港赴台。
彭善在湾里只建有一重两厢的青砖青瓦房,从没置地添产,解放后他家的阶级成分也只划了个“小土地出租”,旧宅一直用做生产队库房。1973年,这座房屋被拆掉改建集体仓库前,还郑重请示了有关部门。新仓库建成后,我曾问老队长:“如果人家回来要,么样赔?”大家只是哈哈一笑。
其实,彭善在汉口江边置有一处大房产,他在内地的三个女儿却从未过问。在武汉的大女儿启皖直说:“别说要回来很麻烦,就是要回来了,台湾那些兄弟姐妹还不回来找麻烦......”
盖棺论定各有褒贬
彭善从排长逐级累功,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等,至1936年2月任陈诚系18军11师师长兼第三十一旅旅长,1939年5月晋升为18军中将军长。抗战胜利后,调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区副总司令、总司令。
老人们讲述最多的,有两件趣事:其一,他从汉口回乡,从不穿官服而着长衫,轿车开到村前里把路就弃车步行,看望穷乡亲还送一两个银元;1948年,横店火车站的一个蒋军连长率兵来砍柏树枝祭清明,正遇到彭善回乡扫墓,他当即命令卫兵拿扁担“把他们往死里打”!
对彭善之褒,主要功绩是奋不顾身抗战打日寇。
1937年,在震惊中外的淞沪会战中,彭善率部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线的防守,面对日军3个师团的猛攻,罗店三次失守,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他不顾劝阻,脱去军大衣,腰配双枪,手端一架德制机关枪亲自上阵,带领敢死队勇猛冲杀,终又夺回阵地。
此后,他又在著名的武汉会战中两立战功;1940年6月初,他率部乘轮船顺长江东下增援宜昌保卫战,与日军激战十多天,至6月12日宜昌沦陷,麾下第十八军再遭重创。
对彭善之贬,主要污点就是在1947年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当年5月,以武汉大学为中心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爱国学潮运动,6月1日凌晨3时,武汉国民党当局调集全副美式装备的军、警、宪、特上千人,突然闯人武汉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宿舍,在与师生发生激烈冲突时,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胡孝扬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手无寸铁的王志德、黄鸣岗、陈如丰3位同学,打伤20多人,逮捕一批进步师生。随即,全国各大城市师生、群众上街游行声讨暴行。当年,各界捐资在武汉大学建“六一惨案”纪念亭。
不久,老蒋和国民党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宣布将胡孝扬等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彭善也被“撤职查办”。他后被改任中央训练团中将副教育长、中将参议等。他曾一度旅居美国,晚年坚决反对“台独”,主张祖国和平统一。
海峡两岸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前,台湾方面曾有意安排彭善担任回大陆参拜的代表团团长,家乡还做了多方面准备,却因他自己“内疚多多”而辞命。
“小台湾”里冤情多
抗战期间,本湾有三位长辈女性偷去延安参加革命,但解放前夕也有几家子弟被国民党强抓壮丁。解放后,因彭善和有人在台湾当兵等缘由,彭郁湾被长期称作“小台湾”,其几房穷亲戚因此在“阶级斗争”年代饱受牵连;到70年代初期,竟有近20名中青男因本湾“名声不好”而难找对象。
其五房侄儿启顺曾担任团小组长等,爱好文艺,二胡拉得好。他说,“文革”不久,被召兵的连长看中,头天已经穿上新军装,当晚为每家挑水以表谢意,次日临出发前却被人告秘而‘取消参军资格’”。
亲眼所见“最遭孽”的,是解放前没跟随彭善去台湾、而在湾里当了上门女婿的松滋勤务兵梁海云。他矮小身个,略有鸡胸、驼背,很像郭沫若名剧《秦始皇》里的主角赢政,因偷卖一点大米换钱,“破坏统购统销政策”,被劳改一年,随后成了挨斗近30年的“老运动员”。他一直干着最重、最累、最脏的农活,还自学了木匠、泥瓦匠等手艺,家家请他经常帮忙尽义务,每年周边村子的荆棘刺棵子都被他砍光当烧柴,大半辈子在忍辱负重中艰难挣扎。
70年代末,县里给“四类分子”摘帽清理名单中,才发现“敌伪档案”里并无此人,所谓“副官”不过就是个端茶倒尿伺候长官的苦役兵。县里曾请他出任政协委员,被婉言谢绝。
寄情书信留影倍思亲
“相逢一笑泯恩仇”。1976年中美解冻后,海峡两岸关系有所缓和。彭善思亲思乡心切,不断托在香港的弟弟鸿运带信,想见三个女儿。1992年春季,其幺女启瑾终于赴台探望,办理了半年期护照,却不满半月就悻悻然回重庆,主因是“二房一家人以为大房人要去争分财产,不太高兴,搞得老人夹在中间很难堪......”
此后,鸿运又催启皖赴港代见。她与父亲的电话交流,还是彭善从亲戚家拨出的。2000年2月14日,享年百岁的他在台湾仙逝。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星期天,我带儿子去武昌水果湖儿童公园玩耍,与照看碰碰车游乐场的慈祥儒雅婆婆聊天,原来彼此早已熟知,她就是小名叫做“甜甜”的启皖阿姨!
今年大年初一下午,启皖阿姨的堂弟启顺叔请我参加他家十多年来的首次团聚会。他拿出一份珍藏的彭善80岁时寻亲书信,是托台湾媒体陈义民老先生转交,另有500美金分送五家亲戚。信封是彭善亲笔书写的繁体楷书,从反复斟酌的“探交”二字中,可见其百般乡愁。他自己和台湾子女的三张合影照片,是后来辗转送给女儿的,都背书了拍摄时间和子女“启”字辈名,可见其良苦用心!
随即,我给启皖阿姨打了一个拜年电话,20多年来她竟一直记得我,一口标准武汉话清脆爽朗,真不像83岁的老太太,健旺得很!
80年代中期以后,几家旅台乡亲的子女陆续返乡寻根。经多方做工作,省里拨款数万元;梁海云的大儿子彭光才已当选副组长,他借新建绕城公路之机,请司机吃饭、给点油钱,把塘堰、公厕等修整一新。
进入新世纪,伴随川龙大道和横店亚洲最大铁路编组站的陆续兴建,原来的彭郁湾已被整整拆掉一半多。前年夏季,已列入武汉名树行列的那棵古柏树,腹部中空处被人丢烟头突然引发火灾,经媒体报道后,竟有台湾乡亲打来关心电话。
这篇“家史、村史钩沉”报道写好后,我又打电话征求启皖阿姨的意见。她在“不想回忆往事”的心酸哽咽中,竟主动提出:“让小儿子传给你一幅我爸爸90年代的照片......”
我在想:这已经不是一位世纪老人及其亲属,以及乡里乡亲来龙去脉的“家史、村史”,它确实牵连着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无限亲情...... (澎潮)
宜昌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