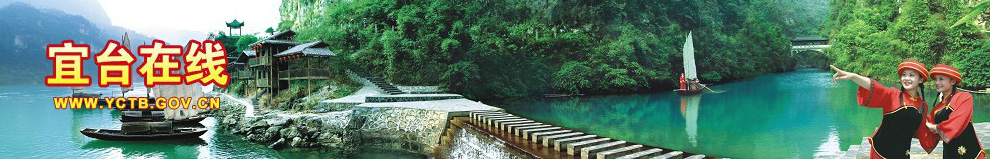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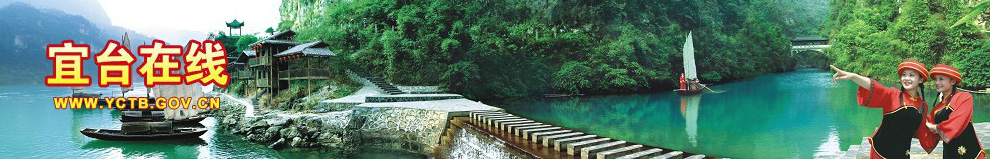
点军区文体旅游局 王蔚
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是她一生的守候
打开那本影集,一张7寸黑白色的全家福照片了然入目,这张照片被奶奶珍藏了多年,覆盖在上面的玻璃纸已然发黄。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8年7月26日。
衬衫、布鞋、花白头发、高高的额头――这位坐在照片最中间的老年男人,便是与奶奶分隔海峡两岸近40年的丈夫。
少女时的奶奶一把大麻花辫子甩在脑后,两只清澈的眼睛眨巴眨巴,明眸皓齿,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待到好女初长成,上门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只是她对那些提亲者不愠不火,不冷不热。直到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个货郎,还带着一个俊秀的儿子,因为大雪封山,天气异常寒冷,不得不在村里借住一个月。奶奶和这个俊俏的男子一见钟情。后来,奶奶曾欢喜地讲,他是读过书的,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或许是因为读书人独特的气质,她对他一见倾心,冲破家庭和族人的重重阻挠,最终她跟随他去了山东。
动乱的年代,幸福不容人把握。山东半岛上一个寻常的夜晚,一阵阵哀嚎打破了小镇的平静,和村里的许多男人一样,他被国民党的军队带走了,从此人事沉浮,杳无音讯。
直至1987年的一天,家里收到了一封台湾寄来的信件,经过多方联络和准备,他要回大陆寻亲了。
记得那天,那张熟悉又陌生的男人的面孔出现在奶奶眼前时,她双唇颤抖,说不出任何语言,只是眼泪如雨点似得往下掉。他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便在他肩头失声痛哭起来。那整整隐埋了四十年的情感瞬间宣泄,佝偻的肩膀在他的怀里起起伏伏呜咽着。四十年的等待,终于换得在他肩头哭泣的一刻。
吃饭时,奶奶坚持要给他用那只青花大瓷碗。家里人告诉他,几十年来,每逢佳节或是平日里家人团聚,那只青花碗就会被拿出来放到桌上,因为奶奶一直坚信:他,还活着。
以为回家无望,他在台湾早已娶妻生子,另建家庭。仅是短暂的一聚便是离别。可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竟是天涯的距离;可叹她一生的守候,“今夜相见,却又碍着你我的白发。”
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是他青春的哀愁。
伯父是家里的长子,大眼睛,浓眉毛,高鼻梁,打小就是父亲一辈儿最聪敏的孩子,自小学习成绩特别好,到小学毕业,都是名列前茅。
爷爷走后,多年不见音讯,奶奶便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家乡。缺少男人的家庭,日子过得总是清苦。要强的奶奶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努力“挣工分”养活一家四口。渐已成年的伯父心痛操劳的母亲,放弃学业,回家挑起生活的重担。村里人看伯父念过书,让他到公社去当会计,爱学习的伯父白天在公社工作,晚上挑灯自习。
当日子渐渐有所起色,又逢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公社工作着,谁料冲进来一帮红卫兵,一边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一边把伯父绑起来,在他头上带上尖尖帽游街示众。他们把他关进一个废弃的猪圈,停水断粮,施尽凌辱让他供述“私通国民党反动派”的事实……
伯父从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走来,练就了他坚毅、乐观的性格。1977年恢复高考后,伯父通过不断努力,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大学时,他和同学相邀去厦门,特意去了一趟厦门环岛路,站在海边,面朝台湾宝岛的方向,一声声呼唤着:“爸爸,爸爸……您在那里吗?爸爸,您听到了么?”两个自他记事以来从未启口的发音冲破喉咙,在海峡间回荡,所有的委屈与哀愁都化作了这两声深情的呼唤。
伯父说当年他被关在猪圈的时候虽然竭力保持自己和家庭的尊严,但也有一丝怨尤在内心深处升腾。他开始质疑自己的父亲,认为他除了带给自己生命就只带给家庭苦难。后来上大学时,无意在图书馆读到于右任先生的《望大陆》,一遍又一遍在口中吟诵: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他说:“父亲也是不易的。”
伯父现在已经退休,每天晚上央视四套《海峡两岸》是他必看的节目。他说等孙子大一点了,自己一定要去台湾走走看看。其实我知道,伯父如同上个世纪中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关于台湾宝岛,除了一丝关己的遗憾还有一股不曾褪去的青春热血,如我经常笑他――事关“一国两制,统一祖国”。
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我生动的旅程。
今年5月中旬,我随点军区经贸考察团到台湾。5月17日下午,我们乘坐的飞机经过2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抵台湾桃园机场上空,由于机场实行流量控制,飞机在桃园上空盘旋一圈又一圈等待落地,坐在窗边的我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探着头想要隔着玻璃、透过云层,一睹宝岛的神秘面容。
坐在身边的同事倒也悠闲,与邻座的美女搭讪起来。听他们聊天才知道,这美女原来是老乡,湖北黄冈人,多年前嫁到桃园,成了台湾媳妇,她说家乡嫁到台湾的人很多。同事转过头来逗我:“你也努把力嫁过去好了。”后来听在台宜昌同乡会陈会长说,当前嫁到台湾的宜昌籍新娘有近3000人。原来两岸的交流与融合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身边且如此频繁。
快到花莲,我们的车停靠在一个小渔港里,准备去觅食,“田妈妈餐厅”――好亲切的名字,简单的2层楼,院里的车倒是停得满满当当。推门进去,挤挤挨挨一屋子人,听口音都是大陆游客。如它的名字一样,整个餐厅只有几个老妈妈在忙碌,跑来跑去盛菜端饭,由于很多内地游客对台湾的一些海产品不了解,老妈妈们一边上菜还一边热情介绍着各种食材。
我们吃完饭正准备离席,导游向我们招手,原来是柜台旁的冰柜上放着我们刚食用的“飞鱼”,一条普通的鱼,背上愣是长出两个小翅膀,可爱极了,我们这群“山里人”立刻拿出相机――拍照!突然有人拍拍我的肩膀,原来是餐厅“阿嬷”,她用软软的台式普通话跟我说:“小姐喔,餐厅后面的水池里有条刚刚打上来的小鲨鱼,要拍照快去喔。”说完胖胖的身姿火速飘过,接着忙活去了。看着“阿嬷”的可爱的背影,心里暖暖的。
在台的7天很快过去了,高高的槟榔树、蓝蓝的太平洋……我从未到过这里,可似乎又从未离开过这里。日月潭、阿里山、基隆港、士林夜市、四四南村、慈湖、绿岛……每到一处我都在静静体会、细细的比较那教科书上的、歌曲中的、故事里的台湾和眼前活色生香的台湾,他们在我的心里相似着各自的相似,缤纷着不同的精彩。
可能是太沉醉于宝岛的秀美风光,快离台的时候,同事不小心将随身挎包遗失,损失惨重,虽报了警,但至今仍然没有音讯……
一年又一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那湾浅浅的海峡不会再成为“她”一生的守候,也不会再成为“他”青春的哀愁。那分明是一个生动的海岛,有“三通直航”的便捷,有大陆新娘的幸福,有餐厅“阿嬷”的热情,也有同事丢包的遗憾……
宜昌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